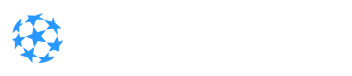常识在司法判决中的运用|新京报 中国学术文摘
作者:365bet体育注册 发布时间:2025-10-31 09: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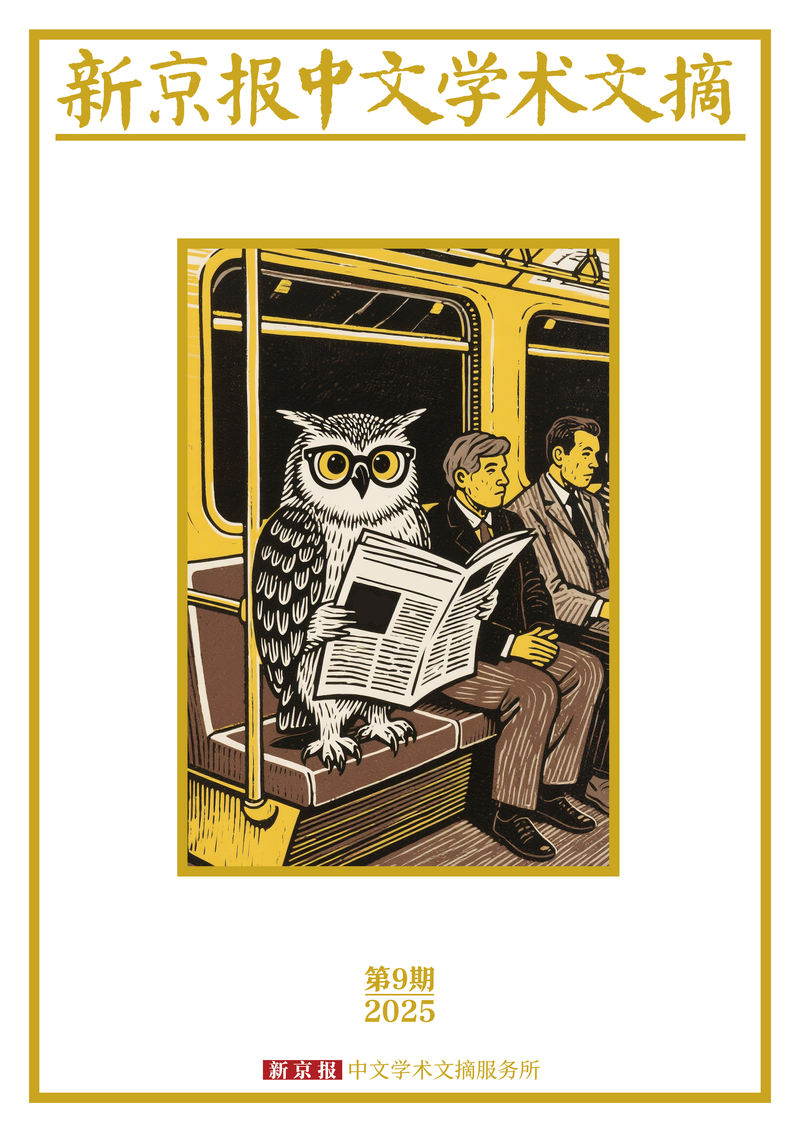 “随着现代技术与常识之间复杂关系的推进和相互竞争,常识的边界不断被重新构成。” ----吴非:《论常识在司法自由裁量权中的运用》,社会科学,2025年第8期,第172-183页,第192页。本期评论:陈新宇黄殿林文字摘录:罗东在当代,除了书籍之外,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是知识生产和知识积累的另一大生产。今年8月以来,《新京报书评周刊》以书评为基础,拓展了“学术评论与文摘”的知识传播,并准备了“新京报中文学术文摘服务”,将人文社会科学与科学、AB期刊资料一起传送到《人大新闻资料抄本》、《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体裁报纸上。每周有一期,每期推荐两篇文章。每期均由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担任审稿人。我们期待向您传递最新的既专业又前沿的论文。我们也希望入选的论文对本土或世界问题有清晰的认识,并对中文写作有独特的态度。这是第9期。第一篇论文的作者吴飞探讨了常识与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关系。按照一般理解,常识就是共同知识,是大多数社会成员(或某种知识专业范围内的大多数从业者)所认可的不言而喻的知识。在司法实践中,当案件的判决结果明显违反一定的定义时,通常会因为不符合人们对公平的期待而受到质疑。常识是社会的基础。不仅有利于司法判决,而且对其作用也有限制使用。笔者以辩证的方法和谨慎的态度来探讨两者的关系。以下内容经社会科学许可转载。有关摘要、表格、参考文献和注释,请参阅原始出版物。作者 |吴非电视剧《以法律之名》(2025)剧照。常识作为日常社会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了人们对人的基本认识,影响着人的社会化水平。从社会整合的角度来看,共同意义构成了人们在社会经验问题上趋于达成共识的重要认知基础,是主体间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司法领域,常识也构成了公众对司法稳定期待的认知和心理基础。司法判决始终应符合常识。但在实践中,一些案件的判决仍与通行判例不一致。不符合常理,甚至严重偏离常识。此前,鄂尔多斯“天价毛衣案”、天津赵华非法持有枪支等事件曾引发争议。近日,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在一起行人碰撞纠纷中使用“未保持安全距离”的表述,引起广泛质疑。法院随后发布了现场视频并道歉以平息争议。这种特殊情况被学者称为“反常识”或“去常识”现象。从案件审理的总体社会效果来看,“反常理”现象的出现,对司法预期的稳定性产生了强烈影响。针对此类问题,学者们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应对思考,针对如何避免常见意义的认知偏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就常见意义的功能和作用达成了共识。常识在司法中的重要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案件受到“反常识”质疑,并不意味着司法判决本身必然存在错误。从规范性来看,常识作为知识体系,具有基础性和普遍性,而对具体案件事实真相的判定则必须具有具体性和具体性。两者之间总是存在着天然的差距。而常识虽然属于每个人,但它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培养。这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当出现一般性问题时,单方面谴责司法判决可能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判断。本文旨在重点探讨通用定义与司法判决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其通用含义,增强司法判决的合法性。具体来说,如果通用含义似乎被认可,可以是否会在司法程序中受到质疑和检验?不同层次的常识如何推动司法自由裁量权标准的制定?在司法判决中运用常识的条件和限制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1、常识的内容层次和基本特征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常常将常识与常识、常识一起使用,其含义几乎等同于“理性”的概念。相比于对常识和常识的语境的依赖,常识的内容具有较强的连续性,普普尔其司法稳定预期更为突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通用定义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是容易的:根据人们的经验,一些通用定义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另一些则在理解上存在争议,这使得其对应关系更加复杂化。在司法案件中,围绕共同含义的误解也会出现。共同意义的复杂特征源于其具体内容。因此,深入探讨常识的内容层面和基本特征,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其独特的价值和在司法裁判中的重要性。 (一)常识的内容层面 常识作为一个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中国古典文学中有“common sense”的表述,通常指普通知识。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常识”一词是日本明治时期创造的新词,19世纪末传入中国并被汉语吸收。根据《汉语词典》的定义,常识是指一般知识。汉语中使用的“一般生活经验”、“经验法则”、“公共秩序和良好礼仪”等概念所以包含一般意义。英语中共同意义的概念是commonsense,源自Sensuscommunis。它最初主要指基于感官的常识和认识。到了现代,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指认知能力人的概念,几乎等同于智慧、睿智、理性、实用主义。陈家英教授认为,中文“Common Sense”重在表面事实,而英文“commonsense”重在事实所蕴含的真相。常识通常涉及对非凡事实的认识和对深刻真理的理解,尤其涉及理论知识和理论体系。 《比较法视角下的证据制度》 作者:[美]Miljian R. Damasca 译者:吴红耀、魏晓娜 等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1 月 根据所学常识内容的水平,经过超越和内化,常识可以分为许多层次。第一个层次,也就是表面的层次,表现为知识,尤其是一些事实的了解。它们来自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属于“经验知识”。第二个层次的常识是基于上述知识记录的某些原则和判断。这些判断是基于对常见事实的理解。如果这些是高度专业和深刻的判断,那么它们并不属于一般理解的范围。第三个层次可以理解为在共同意义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些思想和观念,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良心”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常识为社会个体成员与外界进行精神沟通和价值认同提供了条件。当然,常识的高低是相对的。 “对于人类生活的事实来说,我拥有简单的真理是很困难的。社会的事实和观点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生活的事实本来就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想法创造出来的。”《在可能的生活中》作者:赵廷阳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9月社会人们普遍理解和认可的原则都是在掌握一些基本认识的基础上自己培养出来的。常识中包含的一些判断本身就是共通的。从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用词来看,常识的含义司法文献中的“常识”并没有区分,但两者在评价行为时还是有区别的,“常识”侧重于从理性的角度对人的行为进行分析,而普通的定义则侧重于从认知的角度对人的行为进行分析。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肤浅的认识构成了人们知识体系的主要内容,而判断意义上的常识对人们行为的制约和组织作用则更为突出。常识为人们设定了基本的行为标准,即人们不仅自己遵循常识,而且期望他人也遵循常识。换句话说,违反常识的行为被认为是错误的行为,需要纠正。深刻的理解,即思想或良心意义上的常识,可以作为司法判决的普遍价值指南。我们通常所说的常识是由特定社会所接受的一套信念组成的,该社会的成员认为这些信念是所有理性的人所共有的。不同层次的知识和原理,构成了人类行为的基本规律,体现了人类的共同智慧,是公众产生的最普遍的经验,也是最容易理解的。所有文化中常见的、稳定的和流行的因素。除了内容层次之外,标准定义也有范围限制。我们平时所说的共通意义,就是指生活中的共通意义。某个行业大家都知道的共同定义是对行业的理解,某个专业领域大家都知道的共同含义是专业理解。比如,吸毒会上瘾,这是生活常识;美沙酮维持治疗主要适用于吸食海洛因、注射海洛因的吸毒者,这是禁毒领域的专业理解。通用定义范围的限制不仅体现了其在不同层面的应用价值,也体现了分层化和专家知识化的趋势。在司法裁判中,不同语境下共同含义的准确识别和运用具有重要意义。确保裁决符合一般含义。 (2)常识的不证自明性和可反驳性。一般来说,常识既是不言而喻的,又是可反驳的。常识的不证自明来自于大学和人类理解的直接经验。 《推理》 作者:陈家英 版本:华夏出版社,2011年5月 “因为常识是关于简单、基本的事实和原理,所以通常不需要证明或解释。常识: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从普通知识转变为常识的过程中,经历了多次讨论、误解并完成了其合法性。从社会系统的角度来看,常识为人们认识社会、遵循秩序提供了认知模式和规范基础。它是社会成员共享的认知框架。常识的明显本质使这个过程既经济又方便。在 s社会互动作为简化社会复杂性的重要机制,常识提高了对公共推理的理解和促进社会“有机统一”的实践智慧。从社会成员的行为角度来看,常识的表观性意味着社会成员自然地认识现有的常识并遵循常识,即符合常识的行为是习惯性行为,并不一定反映其行为的合法性。因此,常识的自明性也与常识的直观反应密切相关。如果一个人无法认识自己的感知,无法解释它是如何发生的,甚至无法判断一个行为背后的常识因素,这并不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基于对常识的长期认识,人们通常不需要详细研究常识的具体机制。伊尔。当这种毫无争议的常识状态进入司法程序时,它似乎就具有内在的合法性,无需讨论或证明。然而,常识的表面性是建立在其可靠性的基础上的,总有一些例外和社会例外。 “常识出错的可能性确实非常高,不仅因为时代的变迁,也因为认识的局限性。”在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的推动下,虚拟技术、“元宇宙”等改变了人们对空间的普遍认识;聊天机器人在全球首例AI机器人致人死亡案件中的耐人寻味说辞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人与机器关系的共同理解。多年前,人们普遍认为外出时要特别注意保管现金,以防被盗。移动支付的出现让我们改变了这一点了解。在社会的发展中,社会环境、法律制度等的变化会导致人们产生新的共同含义来取代旧的认识;知识层面的常识也可能发展为经验判断层面的常识;对行业的理解、职业的一般理解和对生活的理解之间存在着动态的交通关系。当行业理解、专业理解被广泛知晓时,它就在生活中变得司空见惯。共同含义的变化状态会对不证自明性产生削弱作用,即某些内容的共同含义在一定时间和场景下是值得怀疑的,人们可能会因接收新信息而感到困惑。对原有共义的动摇,就是对共义的反驳。电影《秋菊打官司》(1992)剧照。如果在通用意义体系内进一步划分,可以确定某个共同含义的可反驳程度。如前所述,常识在内容层面上有多种形式的知识、判断和思想。这背后,人们有着不同程度的共识。对此,可反驳性也存在差异。对于某些有关自然规律的知识或已知事实没有质疑的余地,也不能以不可抗力为由退货。一些表面理解中与生活经历相关的内容,可能会因当事人的年龄、生活经历、所在地等因素而导致共识强度的差异。与城市青年相比,老年农民的农业工作和气象知识更加丰富;华北地区的人们对“顶锅”、“破锅”等丧葬义务也可能有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理解。判决定义中的常识在司法判决中是同质的。它们是相同的规范可以预防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其可反驳性在司法判决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例如,在失业案件中,对于被告人的处境是否感到安心,检察机关认为对货物托运人的约束是其仍具有控制权的表现。因此,上海和深圳航空公司的司机李先生并不想失去工作。但法院认为,按照日常生活常识,用胶带密封纸箱只是用来包装货物,防止散落,不可能达到密封、防盗的目的。李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实际控制着货物,这是其职务的作用。这里检方给出的判决是“封存货物意味着我们仍然拥有控制权”,而法院的判决是“封存货物只是为了防止货物扩散”在此,控、审双方对捆绑物品含义的一般含义存在不同的理解,这种差异是识别被告人主观目的的主要意义。一般情况下,共同含义储存在人们处于明朗状态的结构和意识中,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本案将共同含义提出来讨论,意味着当事人对一些基本内容有不同的看法,也体现了可反驳性。至于常识在概念和价值层面的可反驳性,不言而喻,价值之间的平衡始终是电视剧《底线》(2022)剧照中的一个经典司法问题。与之竞争的共识的强度。常识的“常态”代表了社会的基本共识,是启蒙的部分,而常识的“知识”则是提供不同层次共识及其反驳来源的知识体系。缺乏通用定义意味着不同意使用通用定义。这使得常识推理变得错误,并导致随之而来的争议义务。简而言之,常识的不证自明性赋予了最初的常识以普遍的合法性。当司法裁量权出现争议时,其可反驳必然会产生争议。干预和证据呈现。 2、常识在司法判决中的运用作为法官的重要观点,常识在司法判决中的作用具有普遍性并具有广泛的影响。如果从法律程序的角度将司法程序描述为法律发现,法律发现l 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和法律修辞,常识几乎在整个司法过程中都具有价值。例如,“所有民事法官都会遇到‘表面代理’的判断问题……法官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常识来决定是否援引表面代理制度以及案件中的责任由谁承担,这是常见的做法。” 《法治问题:基层司法观察笔记》 作者:赵耀通 版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年12月 常识是解释正义和普通民众标准的重要依据,促进法律标准与日常生活世界的良性互动。如果将司法判决的形成过程简化为三段论推理,则以案件事实构成推理的小前提,以案件事实适用的法律标准为主要依据,最后以案件事实为依据。判决作为推理的结论,可以发现,常识的作用主要集中在案件的判定上。案件事实是在司法过程中发现和建构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没有必要区分共同定义的应用效果是在建构真理的过程中还是在争论真理的过程中可见。 。人们基于日常生活常识对事实的判断可以在法律体系中固定和规范。这类共义通常是共义体系中最表层的内容,也是最客观的部分。基于对这种常识客观性的信任,立法者通过法律等手段,以法律行为的形式呈现出无可争议的不言而喻的特征,构成了现代司法认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解释[2022]11号)第93号规定,无证据举证,即“自然规律、定理和规律”、“已知事实”和“根据已知事实和日常经验规则推论出的另一事实”均具有自然性“以及”根据已知事实和日常经验规则推论出的另一事实。日常经验规则“都具有共同性。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高检法世字[2019]4号)第四百零一条的规定,将“一般人所熟知的普遍事实”、“自然规律或者规律”作为免责事实。这一司法认知规则是得到司法程序认可的。除了设定一般意义上的免责事实外,在具体案件中,法官还可以进一步细化免责事实的范围。豁免事实based 的情况下的情况。例如,在允许他人服药案件中,二审法官对服用甲基苯丙胺后出现症状的认定是,我国医学研究人员和公安、司法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对各类毒品的物质、性质、滥用方法、症状以及对人体的危害等进行了深入有力的研究,并通过书籍、网站、新闻等方式向公众进行了广泛的禁毒宣传。因此,法院可以通过查阅前述常识信息来判断吸食冰毒的症状,无需额外证据。在知识产权案件中,“常识”可以作为豁免事实。常识是一种专业常识。这是特定领域的专业人员掌握的该领域的通用技术知识。通常是从教科书或技术中获得的专业词典、技术手册等参考书。一些学者将这种“依附于常识并基于常识的证据”称为常识证据,而不是科学证据。常识的含义是通过司法理解作为没有证据的证据来提供证据更加经济,但仅靠司法理解通常无法完成对案件全部事实的认可,而常识的事实部分本质上是人们对事实的理解而不是事实本身,这与自然规律在客观性上有所不同。一方面,这些所包含的事实并不因为不完全客观而失去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被用作证据的可能性。毕竟,只要事实的客观程度不违反司法证明的要求,就可以作为无证据的事实。另一方面,当存在争议时,共同事实能够作为无争议证据的,应当允许质疑方提出证据。需要注意的是,“司法知识的概念不应与背景知识或‘普遍常识’相混淆”。常识性事实可以作为非证据证据,但基于常识或其他生活经验形成的事实不能作为非证据事项,特别是在证明标准严格的刑事司法领域。 《证据评估》作者:[美]特伦斯·安德森等译者:张宝胜朱婷张阅杜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2)通常影响证据的评估“法官如何了解人们的行为和动机”。 《最高人民法院适用
“随着现代技术与常识之间复杂关系的推进和相互竞争,常识的边界不断被重新构成。” ----吴非:《论常识在司法自由裁量权中的运用》,社会科学,2025年第8期,第172-183页,第192页。本期评论:陈新宇黄殿林文字摘录:罗东在当代,除了书籍之外,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是知识生产和知识积累的另一大生产。今年8月以来,《新京报书评周刊》以书评为基础,拓展了“学术评论与文摘”的知识传播,并准备了“新京报中文学术文摘服务”,将人文社会科学与科学、AB期刊资料一起传送到《人大新闻资料抄本》、《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体裁报纸上。每周有一期,每期推荐两篇文章。每期均由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担任审稿人。我们期待向您传递最新的既专业又前沿的论文。我们也希望入选的论文对本土或世界问题有清晰的认识,并对中文写作有独特的态度。这是第9期。第一篇论文的作者吴飞探讨了常识与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关系。按照一般理解,常识就是共同知识,是大多数社会成员(或某种知识专业范围内的大多数从业者)所认可的不言而喻的知识。在司法实践中,当案件的判决结果明显违反一定的定义时,通常会因为不符合人们对公平的期待而受到质疑。常识是社会的基础。不仅有利于司法判决,而且对其作用也有限制使用。笔者以辩证的方法和谨慎的态度来探讨两者的关系。以下内容经社会科学许可转载。有关摘要、表格、参考文献和注释,请参阅原始出版物。作者 |吴非电视剧《以法律之名》(2025)剧照。常识作为日常社会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了人们对人的基本认识,影响着人的社会化水平。从社会整合的角度来看,共同意义构成了人们在社会经验问题上趋于达成共识的重要认知基础,是主体间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司法领域,常识也构成了公众对司法稳定期待的认知和心理基础。司法判决始终应符合常识。但在实践中,一些案件的判决仍与通行判例不一致。不符合常理,甚至严重偏离常识。此前,鄂尔多斯“天价毛衣案”、天津赵华非法持有枪支等事件曾引发争议。近日,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在一起行人碰撞纠纷中使用“未保持安全距离”的表述,引起广泛质疑。法院随后发布了现场视频并道歉以平息争议。这种特殊情况被学者称为“反常识”或“去常识”现象。从案件审理的总体社会效果来看,“反常理”现象的出现,对司法预期的稳定性产生了强烈影响。针对此类问题,学者们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应对思考,针对如何避免常见意义的认知偏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就常见意义的功能和作用达成了共识。常识在司法中的重要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案件受到“反常识”质疑,并不意味着司法判决本身必然存在错误。从规范性来看,常识作为知识体系,具有基础性和普遍性,而对具体案件事实真相的判定则必须具有具体性和具体性。两者之间总是存在着天然的差距。而常识虽然属于每个人,但它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培养。这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当出现一般性问题时,单方面谴责司法判决可能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判断。本文旨在重点探讨通用定义与司法判决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其通用含义,增强司法判决的合法性。具体来说,如果通用含义似乎被认可,可以是否会在司法程序中受到质疑和检验?不同层次的常识如何推动司法自由裁量权标准的制定?在司法判决中运用常识的条件和限制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1、常识的内容层次和基本特征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常常将常识与常识、常识一起使用,其含义几乎等同于“理性”的概念。相比于对常识和常识的语境的依赖,常识的内容具有较强的连续性,普普尔其司法稳定预期更为突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通用定义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是容易的:根据人们的经验,一些通用定义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另一些则在理解上存在争议,这使得其对应关系更加复杂化。在司法案件中,围绕共同含义的误解也会出现。共同意义的复杂特征源于其具体内容。因此,深入探讨常识的内容层面和基本特征,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其独特的价值和在司法裁判中的重要性。 (一)常识的内容层面 常识作为一个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中国古典文学中有“common sense”的表述,通常指普通知识。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常识”一词是日本明治时期创造的新词,19世纪末传入中国并被汉语吸收。根据《汉语词典》的定义,常识是指一般知识。汉语中使用的“一般生活经验”、“经验法则”、“公共秩序和良好礼仪”等概念所以包含一般意义。英语中共同意义的概念是commonsense,源自Sensuscommunis。它最初主要指基于感官的常识和认识。到了现代,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指认知能力人的概念,几乎等同于智慧、睿智、理性、实用主义。陈家英教授认为,中文“Common Sense”重在表面事实,而英文“commonsense”重在事实所蕴含的真相。常识通常涉及对非凡事实的认识和对深刻真理的理解,尤其涉及理论知识和理论体系。 《比较法视角下的证据制度》 作者:[美]Miljian R. Damasca 译者:吴红耀、魏晓娜 等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1 月 根据所学常识内容的水平,经过超越和内化,常识可以分为许多层次。第一个层次,也就是表面的层次,表现为知识,尤其是一些事实的了解。它们来自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属于“经验知识”。第二个层次的常识是基于上述知识记录的某些原则和判断。这些判断是基于对常见事实的理解。如果这些是高度专业和深刻的判断,那么它们并不属于一般理解的范围。第三个层次可以理解为在共同意义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些思想和观念,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良心”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常识为社会个体成员与外界进行精神沟通和价值认同提供了条件。当然,常识的高低是相对的。 “对于人类生活的事实来说,我拥有简单的真理是很困难的。社会的事实和观点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生活的事实本来就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想法创造出来的。”《在可能的生活中》作者:赵廷阳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9月社会人们普遍理解和认可的原则都是在掌握一些基本认识的基础上自己培养出来的。常识中包含的一些判断本身就是共通的。从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用词来看,常识的含义司法文献中的“常识”并没有区分,但两者在评价行为时还是有区别的,“常识”侧重于从理性的角度对人的行为进行分析,而普通的定义则侧重于从认知的角度对人的行为进行分析。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肤浅的认识构成了人们知识体系的主要内容,而判断意义上的常识对人们行为的制约和组织作用则更为突出。常识为人们设定了基本的行为标准,即人们不仅自己遵循常识,而且期望他人也遵循常识。换句话说,违反常识的行为被认为是错误的行为,需要纠正。深刻的理解,即思想或良心意义上的常识,可以作为司法判决的普遍价值指南。我们通常所说的常识是由特定社会所接受的一套信念组成的,该社会的成员认为这些信念是所有理性的人所共有的。不同层次的知识和原理,构成了人类行为的基本规律,体现了人类的共同智慧,是公众产生的最普遍的经验,也是最容易理解的。所有文化中常见的、稳定的和流行的因素。除了内容层次之外,标准定义也有范围限制。我们平时所说的共通意义,就是指生活中的共通意义。某个行业大家都知道的共同定义是对行业的理解,某个专业领域大家都知道的共同含义是专业理解。比如,吸毒会上瘾,这是生活常识;美沙酮维持治疗主要适用于吸食海洛因、注射海洛因的吸毒者,这是禁毒领域的专业理解。通用定义范围的限制不仅体现了其在不同层面的应用价值,也体现了分层化和专家知识化的趋势。在司法裁判中,不同语境下共同含义的准确识别和运用具有重要意义。确保裁决符合一般含义。 (2)常识的不证自明性和可反驳性。一般来说,常识既是不言而喻的,又是可反驳的。常识的不证自明来自于大学和人类理解的直接经验。 《推理》 作者:陈家英 版本:华夏出版社,2011年5月 “因为常识是关于简单、基本的事实和原理,所以通常不需要证明或解释。常识: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从普通知识转变为常识的过程中,经历了多次讨论、误解并完成了其合法性。从社会系统的角度来看,常识为人们认识社会、遵循秩序提供了认知模式和规范基础。它是社会成员共享的认知框架。常识的明显本质使这个过程既经济又方便。在 s社会互动作为简化社会复杂性的重要机制,常识提高了对公共推理的理解和促进社会“有机统一”的实践智慧。从社会成员的行为角度来看,常识的表观性意味着社会成员自然地认识现有的常识并遵循常识,即符合常识的行为是习惯性行为,并不一定反映其行为的合法性。因此,常识的自明性也与常识的直观反应密切相关。如果一个人无法认识自己的感知,无法解释它是如何发生的,甚至无法判断一个行为背后的常识因素,这并不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基于对常识的长期认识,人们通常不需要详细研究常识的具体机制。伊尔。当这种毫无争议的常识状态进入司法程序时,它似乎就具有内在的合法性,无需讨论或证明。然而,常识的表面性是建立在其可靠性的基础上的,总有一些例外和社会例外。 “常识出错的可能性确实非常高,不仅因为时代的变迁,也因为认识的局限性。”在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的推动下,虚拟技术、“元宇宙”等改变了人们对空间的普遍认识;聊天机器人在全球首例AI机器人致人死亡案件中的耐人寻味说辞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人与机器关系的共同理解。多年前,人们普遍认为外出时要特别注意保管现金,以防被盗。移动支付的出现让我们改变了这一点了解。在社会的发展中,社会环境、法律制度等的变化会导致人们产生新的共同含义来取代旧的认识;知识层面的常识也可能发展为经验判断层面的常识;对行业的理解、职业的一般理解和对生活的理解之间存在着动态的交通关系。当行业理解、专业理解被广泛知晓时,它就在生活中变得司空见惯。共同含义的变化状态会对不证自明性产生削弱作用,即某些内容的共同含义在一定时间和场景下是值得怀疑的,人们可能会因接收新信息而感到困惑。对原有共义的动摇,就是对共义的反驳。电影《秋菊打官司》(1992)剧照。如果在通用意义体系内进一步划分,可以确定某个共同含义的可反驳程度。如前所述,常识在内容层面上有多种形式的知识、判断和思想。这背后,人们有着不同程度的共识。对此,可反驳性也存在差异。对于某些有关自然规律的知识或已知事实没有质疑的余地,也不能以不可抗力为由退货。一些表面理解中与生活经历相关的内容,可能会因当事人的年龄、生活经历、所在地等因素而导致共识强度的差异。与城市青年相比,老年农民的农业工作和气象知识更加丰富;华北地区的人们对“顶锅”、“破锅”等丧葬义务也可能有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理解。判决定义中的常识在司法判决中是同质的。它们是相同的规范可以预防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其可反驳性在司法判决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例如,在失业案件中,对于被告人的处境是否感到安心,检察机关认为对货物托运人的约束是其仍具有控制权的表现。因此,上海和深圳航空公司的司机李先生并不想失去工作。但法院认为,按照日常生活常识,用胶带密封纸箱只是用来包装货物,防止散落,不可能达到密封、防盗的目的。李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实际控制着货物,这是其职务的作用。这里检方给出的判决是“封存货物意味着我们仍然拥有控制权”,而法院的判决是“封存货物只是为了防止货物扩散”在此,控、审双方对捆绑物品含义的一般含义存在不同的理解,这种差异是识别被告人主观目的的主要意义。一般情况下,共同含义储存在人们处于明朗状态的结构和意识中,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本案将共同含义提出来讨论,意味着当事人对一些基本内容有不同的看法,也体现了可反驳性。至于常识在概念和价值层面的可反驳性,不言而喻,价值之间的平衡始终是电视剧《底线》(2022)剧照中的一个经典司法问题。与之竞争的共识的强度。常识的“常态”代表了社会的基本共识,是启蒙的部分,而常识的“知识”则是提供不同层次共识及其反驳来源的知识体系。缺乏通用定义意味着不同意使用通用定义。这使得常识推理变得错误,并导致随之而来的争议义务。简而言之,常识的不证自明性赋予了最初的常识以普遍的合法性。当司法裁量权出现争议时,其可反驳必然会产生争议。干预和证据呈现。 2、常识在司法判决中的运用作为法官的重要观点,常识在司法判决中的作用具有普遍性并具有广泛的影响。如果从法律程序的角度将司法程序描述为法律发现,法律发现l 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和法律修辞,常识几乎在整个司法过程中都具有价值。例如,“所有民事法官都会遇到‘表面代理’的判断问题……法官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常识来决定是否援引表面代理制度以及案件中的责任由谁承担,这是常见的做法。” 《法治问题:基层司法观察笔记》 作者:赵耀通 版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年12月 常识是解释正义和普通民众标准的重要依据,促进法律标准与日常生活世界的良性互动。如果将司法判决的形成过程简化为三段论推理,则以案件事实构成推理的小前提,以案件事实适用的法律标准为主要依据,最后以案件事实为依据。判决作为推理的结论,可以发现,常识的作用主要集中在案件的判定上。案件事实是在司法过程中发现和建构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没有必要区分共同定义的应用效果是在建构真理的过程中还是在争论真理的过程中可见。 。人们基于日常生活常识对事实的判断可以在法律体系中固定和规范。这类共义通常是共义体系中最表层的内容,也是最客观的部分。基于对这种常识客观性的信任,立法者通过法律等手段,以法律行为的形式呈现出无可争议的不言而喻的特征,构成了现代司法认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解释[2022]11号)第93号规定,无证据举证,即“自然规律、定理和规律”、“已知事实”和“根据已知事实和日常经验规则推论出的另一事实”均具有自然性“以及”根据已知事实和日常经验规则推论出的另一事实。日常经验规则“都具有共同性。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高检法世字[2019]4号)第四百零一条的规定,将“一般人所熟知的普遍事实”、“自然规律或者规律”作为免责事实。这一司法认知规则是得到司法程序认可的。除了设定一般意义上的免责事实外,在具体案件中,法官还可以进一步细化免责事实的范围。豁免事实based 的情况下的情况。例如,在允许他人服药案件中,二审法官对服用甲基苯丙胺后出现症状的认定是,我国医学研究人员和公安、司法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对各类毒品的物质、性质、滥用方法、症状以及对人体的危害等进行了深入有力的研究,并通过书籍、网站、新闻等方式向公众进行了广泛的禁毒宣传。因此,法院可以通过查阅前述常识信息来判断吸食冰毒的症状,无需额外证据。在知识产权案件中,“常识”可以作为豁免事实。常识是一种专业常识。这是特定领域的专业人员掌握的该领域的通用技术知识。通常是从教科书或技术中获得的专业词典、技术手册等参考书。一些学者将这种“依附于常识并基于常识的证据”称为常识证据,而不是科学证据。常识的含义是通过司法理解作为没有证据的证据来提供证据更加经济,但仅靠司法理解通常无法完成对案件全部事实的认可,而常识的事实部分本质上是人们对事实的理解而不是事实本身,这与自然规律在客观性上有所不同。一方面,这些所包含的事实并不因为不完全客观而失去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被用作证据的可能性。毕竟,只要事实的客观程度不违反司法证明的要求,就可以作为无证据的事实。另一方面,当存在争议时,共同事实能够作为无争议证据的,应当允许质疑方提出证据。需要注意的是,“司法知识的概念不应与背景知识或‘普遍常识’相混淆”。常识性事实可以作为非证据证据,但基于常识或其他生活经验形成的事实不能作为非证据事项,特别是在证明标准严格的刑事司法领域。 《证据评估》作者:[美]特伦斯·安德森等译者:张宝胜朱婷张阅杜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2)通常影响证据的评估“法官如何了解人们的行为和动机”。 《最高人民法院适用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