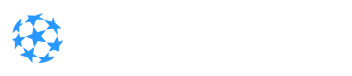“安史之乱”:经典的新运用 - 新京报
作者:bet356体育官方网站 发布时间:2025-11-05 09:27
 从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学”的角度来看,安史之乱恰好是文明兴衰的临界点。以前的唐朝,由于有李白、杜甫、玄奘、惠能等人的存在,堪称古典文明的顶峰。强大的国力和令人愉快的行为成为后人想象盛世的典范。安史叛乱的爆发就像奥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一样,破坏了帝国的政治秩序,抹去了古典文明的理想形象。千百年来,学术界对安史之乱的兴衰争论不休。但由于传统政治史叙事的局限性,这一主题的叙事往往局限于《资治通鉴》所设定的框架,集中于帝王将相的决策和政治权谋的博弈。他们未能逃脱摆脱线性历史视角的束缚,对历史深层次结构性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直到近几年,唐史研究领域才开始出现方法创新。例如,李必言的《危机与重建:唐帝国与地方诸侯》从区域政治变迁的角度重建了唐中后期地方权力结构演变的内在逻辑; 《仇路明与河北文化》《中晚唐政治与文化》运用墓志铭、雕刻等新文献,结合史料,从政治集团思维和政治惯性的角度探讨诸侯城镇格局;历史作家张明阳的《弃长安》用文学叙事囊括了最新的学术成果。当学术界普遍认为安史之乱的研究已经达到瓶颈时,十九世纪末,物理学家们完成了“物理学的大厦基本完成”,《安史之乱:历史、宣传和神话》(这里简称《胡克奇之乱》)由张发和胡克奇合着,独树一帜。本书在邱路明等学者研究遗产的基础上,引入经济学、社会学、军事学等跨学科方法,沿袭欧罗巴经典研究的建模方法,为安史之乱研究开辟了新的学术空间。堪称近年来唐史研究领域的杰作。唐代作品《明帝游蜀》部分(李兆道插图)。 《安史之乱》作者:张世平胡克奇版本:世纪文学风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致力于地缘经济格局演变传统历史解读的历史安史之乱的起因多集中于唐玄宗晚年的疏政、李林甫、杨过的忠权等布罗代尔,而“安史之乱”借鉴了费尔南·布罗的“长期”理论,着眼于秦汉至隋唐的地缘经济格局的演变,揭示了导致安史之乱的深层结构性冲突。叛乱爆发。作者指出,秦汉时期以关中为统治根据地,是由于当时关中平原的经济优势所致。关中地区充足的粮食和密集的人口,为朝廷控制四方提供了物质支撑。但东汉以来,河北逐渐完成经济一体化,经济和人口逐渐超过关中。前秦灭前燕时,河北百姓面积和经济实力均是关中的三倍以上。经济和地理的失衡导致了隋唐时期长期的社会冲突。掌握大权的关陇集团,依然沿袭关中标准。结果,河北虽有“殷富物产,其民为佳之地”,但长期处于政治资源配置的边缘。河北士人崛起的渠道狭窄,难以进入权力核心。同时,东南地区的经济崛起,催生了新的商业格局,南方的丝绸、盐茶等商品,换取北方的物产产生了较大的溢价。河北虽然农业发达,人口众多,但通过商业实现阶级的可能性不大。河北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在藩镇当兵,夺取经济利益和权利。他们对朝廷的不满逐渐积累,为叛乱的爆发和随后诸侯割据的统治埋下了伏笔。笔者进一步分析,玄宗中期以后,唐朝与吐蕃长期战乱,导致西方军事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在边境地区,河北军镇的军需物资不断减少。这种战略倾斜加剧了当地军民的不满。上述因素共同构成了安史之乱爆发的“基本条件”,作者的分析框架显示出很强的长远历史视角的叙述能力。 《安史之乱》的一大亮点就是跨学科的手法。可能是马来人应用的方法。作者不仅引入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来分析宏观背景,还凭借自己深厚的欧洲阶级理论科学素养和军事知识对历史细节进行微观解构,为许多有争议的历史问题提供更加理性的结论。在对李林甫与杨国忠的研究中,笔者运用“历史数量”的方法对李林甫上台前进行比较。唐代后期的纳税人口数据表明,尽管李林甫的私德、户政和赋税改革颇受争议,但他实施的纳税人口数量却是唐朝控制的纳税人口的两倍,有效缓解了玄宗时代的财政危机。话说回来,李林甫确实是帮助唐玄宗克服财政困难的重要助手,可以说是一位激进的改革家。至于杨国忠的崛起。作者指出,杨国忠只是杨贵妃的远房亲戚,他的崛起与之无关。杨国忠的崛起本质上是“权力结构调整和改革”的结果。唐玄宗因其出色的财务管理技巧而器重他。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对军事问题的讨论,这对大多数历史记述来说并不重要。学者们在历史上遇到战争时,只能引用某些战略理论来进行笼统的解释。本书的第一作者张士平不仅对战争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分析,而且还根据具体的地形和地形进行了战术分析。本书使用了许多军事地图来解释战争,书中将很多令后世迷惑的战事与地理特征相结合,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所指出的那样,唐朝的官方史料很多都是出于政治目的的宣传材料,而且很多都是混杂的记载,仅依靠传统的历史研究很难辨别真伪。方法。然而,作者用军事科学的原理来验证史实,用“基本军事逻辑”来验证史料,谜团一下子就明朗了。尤为难得的是,与一般军事学者相比,本书作者特别关注战争的场外因素,如政治动向、财政状况、后勤保障等。例如,唐玄宗鼓励弟弟蜀汉出潼关与燕军作战。这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重大错误,导致一场本来可以在一年内平息的叛乱持续到八年之久。书中指出,当时唐玄宗力劝哥舒翰出境决战,不仅是因为他对哥舒翰的忠诚心存怀疑,更重要的是因为封常清等人的错误,导致唐朝失去了洛阳和陕西郡,两条主要水运,还有南港、水支、军队附近的重要城镇。唐玄宗只能逼迫弟弟蜀汉主动打破僵局。又如:阿庆绪输了两章后就逃离众人,甚至史思明也曾宣布投降。然而唐朝在香积寺、新店两次决战获胜后,却滞留兵力一年,并未乘胜追击。这给了史思明等人再次造反的机会。因此,唐朝未能取得彻底的胜利。对于这一奇怪的现象,本书汇集了唐朝的财政状况,并指出当时所用的是前一年征收的江南赋税。由于所有筹集军事费用的财政手段都已耗尽,唐朝正处于缺钱、停止进攻的边缘。这种研究方法结合了军事情报的分析结合政治、金融背景,不仅还原了历史真相,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启发方法。跨学科方法的引入为许多历史上未解决的案件提供了简单而直接的解决方案。作者对张勋吃人、保卫睢阳城一案的重新审视,堪称经典案例。相传张巡在睢阳之战中“杀妻宴妾”,吃人数万人。这一记录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忠君报国”的极端案例,也引发了后世关于“道德伦理与生存”的争议。作者采用“定量分析”与“逻辑推理”相结合的方法,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严谨的研究:首先,通过对绥城内储存的粮食、士兵和人员数量的记录进行分类他根据史料计算,原来的六万粒粮食,足以供养六千八百名守城士兵一年。之后,一半以上的粮食都分配给了其他城市和守城的人们。不过,随着守城士兵的减少,口粮的缺乏并没有传说中那么严重。其次,作者指出,南霁云第二次求援后,1000多名援军带来了数百头牛、数匹马参战,进一步缓解了粮食短缺的压力。看来没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同类相食。甚至在拿到这批牛之前,在粮草最困难的时候,守军就进行了小规模的吃人行为。两千名守军,两个月之内吃掉几千人,那是不可能的。正如张巡的好友李翰明确指出的那样,“损失数百人,代价是天下”。乙综合上述证据,笔者得出结论,吃人事件发生在张巡城期间,但主要发生在断粮时。在平民中,守军并没有进行有组织规模的吃人行为。这项研究不仅还原了历史真相,也揭示了“历史叙事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历史叙事往往包含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唐朝官方夸大张巡吃人事件,塑造“忠君报国”的道德典范。后世文人以此叙事构建了“普遍伦理高于个体生命”的价值体系。在古人看来,经过他们的夸张,张巡的行为更加极端,也更加符合偏执的道德叙事。然而,现代人很难理解这种野蛮的偏执。这对“安史之乱”的研究,通过历史细节的定量分析和逻辑验证,破译了宣传造成的恐怖故事,成功为张勋辩护。 《安史之乱》在学术价值和阅读体验之间取得了平衡。它既是专业研究人员的学术著作,也是普通历史爱好者的热门读物。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本书的美妙之处在于作者“宏观视野与微观细节相结合”的叙事方法,不仅在“千年时间尺度、万里地理空间”内冷静解读安史之乱的历史脉络,而且研究历史细节,解决历史悬案,愉悦读者思考历史。对于专业研究人员来说,本书的价值在于将地缘经济、军事战略、财政制度等维度融入到分析框架中,继承欧洲古典传统,拓展了安史之乱的研究视野。撰文:周鲁峰 编辑:罗东 李阳 校对:薛景宁
从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学”的角度来看,安史之乱恰好是文明兴衰的临界点。以前的唐朝,由于有李白、杜甫、玄奘、惠能等人的存在,堪称古典文明的顶峰。强大的国力和令人愉快的行为成为后人想象盛世的典范。安史叛乱的爆发就像奥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一样,破坏了帝国的政治秩序,抹去了古典文明的理想形象。千百年来,学术界对安史之乱的兴衰争论不休。但由于传统政治史叙事的局限性,这一主题的叙事往往局限于《资治通鉴》所设定的框架,集中于帝王将相的决策和政治权谋的博弈。他们未能逃脱摆脱线性历史视角的束缚,对历史深层次结构性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直到近几年,唐史研究领域才开始出现方法创新。例如,李必言的《危机与重建:唐帝国与地方诸侯》从区域政治变迁的角度重建了唐中后期地方权力结构演变的内在逻辑; 《仇路明与河北文化》《中晚唐政治与文化》运用墓志铭、雕刻等新文献,结合史料,从政治集团思维和政治惯性的角度探讨诸侯城镇格局;历史作家张明阳的《弃长安》用文学叙事囊括了最新的学术成果。当学术界普遍认为安史之乱的研究已经达到瓶颈时,十九世纪末,物理学家们完成了“物理学的大厦基本完成”,《安史之乱:历史、宣传和神话》(这里简称《胡克奇之乱》)由张发和胡克奇合着,独树一帜。本书在邱路明等学者研究遗产的基础上,引入经济学、社会学、军事学等跨学科方法,沿袭欧罗巴经典研究的建模方法,为安史之乱研究开辟了新的学术空间。堪称近年来唐史研究领域的杰作。唐代作品《明帝游蜀》部分(李兆道插图)。 《安史之乱》作者:张世平胡克奇版本:世纪文学风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致力于地缘经济格局演变传统历史解读的历史安史之乱的起因多集中于唐玄宗晚年的疏政、李林甫、杨过的忠权等布罗代尔,而“安史之乱”借鉴了费尔南·布罗的“长期”理论,着眼于秦汉至隋唐的地缘经济格局的演变,揭示了导致安史之乱的深层结构性冲突。叛乱爆发。作者指出,秦汉时期以关中为统治根据地,是由于当时关中平原的经济优势所致。关中地区充足的粮食和密集的人口,为朝廷控制四方提供了物质支撑。但东汉以来,河北逐渐完成经济一体化,经济和人口逐渐超过关中。前秦灭前燕时,河北百姓面积和经济实力均是关中的三倍以上。经济和地理的失衡导致了隋唐时期长期的社会冲突。掌握大权的关陇集团,依然沿袭关中标准。结果,河北虽有“殷富物产,其民为佳之地”,但长期处于政治资源配置的边缘。河北士人崛起的渠道狭窄,难以进入权力核心。同时,东南地区的经济崛起,催生了新的商业格局,南方的丝绸、盐茶等商品,换取北方的物产产生了较大的溢价。河北虽然农业发达,人口众多,但通过商业实现阶级的可能性不大。河北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在藩镇当兵,夺取经济利益和权利。他们对朝廷的不满逐渐积累,为叛乱的爆发和随后诸侯割据的统治埋下了伏笔。笔者进一步分析,玄宗中期以后,唐朝与吐蕃长期战乱,导致西方军事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在边境地区,河北军镇的军需物资不断减少。这种战略倾斜加剧了当地军民的不满。上述因素共同构成了安史之乱爆发的“基本条件”,作者的分析框架显示出很强的长远历史视角的叙述能力。 《安史之乱》的一大亮点就是跨学科的手法。可能是马来人应用的方法。作者不仅引入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来分析宏观背景,还凭借自己深厚的欧洲阶级理论科学素养和军事知识对历史细节进行微观解构,为许多有争议的历史问题提供更加理性的结论。在对李林甫与杨国忠的研究中,笔者运用“历史数量”的方法对李林甫上台前进行比较。唐代后期的纳税人口数据表明,尽管李林甫的私德、户政和赋税改革颇受争议,但他实施的纳税人口数量却是唐朝控制的纳税人口的两倍,有效缓解了玄宗时代的财政危机。话说回来,李林甫确实是帮助唐玄宗克服财政困难的重要助手,可以说是一位激进的改革家。至于杨国忠的崛起。作者指出,杨国忠只是杨贵妃的远房亲戚,他的崛起与之无关。杨国忠的崛起本质上是“权力结构调整和改革”的结果。唐玄宗因其出色的财务管理技巧而器重他。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对军事问题的讨论,这对大多数历史记述来说并不重要。学者们在历史上遇到战争时,只能引用某些战略理论来进行笼统的解释。本书的第一作者张士平不仅对战争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分析,而且还根据具体的地形和地形进行了战术分析。本书使用了许多军事地图来解释战争,书中将很多令后世迷惑的战事与地理特征相结合,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所指出的那样,唐朝的官方史料很多都是出于政治目的的宣传材料,而且很多都是混杂的记载,仅依靠传统的历史研究很难辨别真伪。方法。然而,作者用军事科学的原理来验证史实,用“基本军事逻辑”来验证史料,谜团一下子就明朗了。尤为难得的是,与一般军事学者相比,本书作者特别关注战争的场外因素,如政治动向、财政状况、后勤保障等。例如,唐玄宗鼓励弟弟蜀汉出潼关与燕军作战。这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重大错误,导致一场本来可以在一年内平息的叛乱持续到八年之久。书中指出,当时唐玄宗力劝哥舒翰出境决战,不仅是因为他对哥舒翰的忠诚心存怀疑,更重要的是因为封常清等人的错误,导致唐朝失去了洛阳和陕西郡,两条主要水运,还有南港、水支、军队附近的重要城镇。唐玄宗只能逼迫弟弟蜀汉主动打破僵局。又如:阿庆绪输了两章后就逃离众人,甚至史思明也曾宣布投降。然而唐朝在香积寺、新店两次决战获胜后,却滞留兵力一年,并未乘胜追击。这给了史思明等人再次造反的机会。因此,唐朝未能取得彻底的胜利。对于这一奇怪的现象,本书汇集了唐朝的财政状况,并指出当时所用的是前一年征收的江南赋税。由于所有筹集军事费用的财政手段都已耗尽,唐朝正处于缺钱、停止进攻的边缘。这种研究方法结合了军事情报的分析结合政治、金融背景,不仅还原了历史真相,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启发方法。跨学科方法的引入为许多历史上未解决的案件提供了简单而直接的解决方案。作者对张勋吃人、保卫睢阳城一案的重新审视,堪称经典案例。相传张巡在睢阳之战中“杀妻宴妾”,吃人数万人。这一记录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忠君报国”的极端案例,也引发了后世关于“道德伦理与生存”的争议。作者采用“定量分析”与“逻辑推理”相结合的方法,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严谨的研究:首先,通过对绥城内储存的粮食、士兵和人员数量的记录进行分类他根据史料计算,原来的六万粒粮食,足以供养六千八百名守城士兵一年。之后,一半以上的粮食都分配给了其他城市和守城的人们。不过,随着守城士兵的减少,口粮的缺乏并没有传说中那么严重。其次,作者指出,南霁云第二次求援后,1000多名援军带来了数百头牛、数匹马参战,进一步缓解了粮食短缺的压力。看来没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同类相食。甚至在拿到这批牛之前,在粮草最困难的时候,守军就进行了小规模的吃人行为。两千名守军,两个月之内吃掉几千人,那是不可能的。正如张巡的好友李翰明确指出的那样,“损失数百人,代价是天下”。乙综合上述证据,笔者得出结论,吃人事件发生在张巡城期间,但主要发生在断粮时。在平民中,守军并没有进行有组织规模的吃人行为。这项研究不仅还原了历史真相,也揭示了“历史叙事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历史叙事往往包含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唐朝官方夸大张巡吃人事件,塑造“忠君报国”的道德典范。后世文人以此叙事构建了“普遍伦理高于个体生命”的价值体系。在古人看来,经过他们的夸张,张巡的行为更加极端,也更加符合偏执的道德叙事。然而,现代人很难理解这种野蛮的偏执。这对“安史之乱”的研究,通过历史细节的定量分析和逻辑验证,破译了宣传造成的恐怖故事,成功为张勋辩护。 《安史之乱》在学术价值和阅读体验之间取得了平衡。它既是专业研究人员的学术著作,也是普通历史爱好者的热门读物。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本书的美妙之处在于作者“宏观视野与微观细节相结合”的叙事方法,不仅在“千年时间尺度、万里地理空间”内冷静解读安史之乱的历史脉络,而且研究历史细节,解决历史悬案,愉悦读者思考历史。对于专业研究人员来说,本书的价值在于将地缘经济、军事战略、财政制度等维度融入到分析框架中,继承欧洲古典传统,拓展了安史之乱的研究视野。撰文:周鲁峰 编辑:罗东 李阳 校对:薛景宁 上一篇:韩长发接受调查 - 新京报
下一篇:没有了